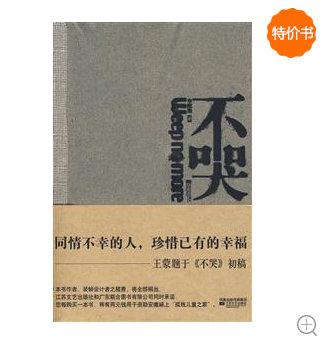不哭申赋渔
¥11.7 3年前 中图网 领券购买
本书内容包括:宝宝,不哭、为了孩子去流浪、孤儿院、9月1日、压跨的18岁、宏雅的微笑、14岁,15岁、血色少年、城市边上等。
节选:
宝宝,不哭
她才一岁半,父亲把她一个人,丢在医院。
麻醉过后。光亮一点点从她的眼睛里消失,熄灭了。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,在慢慢合上之后,缓缓地,从眼角落下。
病房很大,静静的。一个小不点,孤零零地躺着,床显得特别大。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,她就是那个受伤的,一岁半的女孩。她张了张嘴,想哭,脸上挂着泪。她的父亲送她到医院,就走了,不再出现。留下她一个人,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。
她的一条腿缠着绷带,悬空吊在架子上,架子很高。她全身都裹了绷带。她这样躺着已经一个月,身边没有亲人。
“42%的面积被烧伤,35%是三度重伤。”主治医生说。
女孩哭起来。
护士摸摸她的手:“宝宝不哭。”
医生说:“宝宝不哭。”
我也说:“宝宝不哭。”
孩子哭得更厉害,喊:“妈妈,妈妈。”
妈妈不在。没有人知道,她还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,她的爸爸。没有人知道她是谁,她的家人是谁。她一个人,被丢在医院。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2004年3月9日。白下路,南京红十字医院。
晚上8点,7病区,烧伤科。门卫打来电话:一个小女孩烧伤,很重。护士赶忙下楼,去接。
“我到一楼电梯口,两个男的,前面那人手里抱着个孩子。用棉被严严实实地裹着。上了电梯,他说两天前火烫的。小孩她妈妈回四川老家弄钱了。他在镇江打工。孩子在句容医院治过。医生让转来这里。那人后面跟着的是他朋友。”护士说。
病区处置室。乔骋医生已经在这里等,他是烧伤科主任。“烧得非常重,非常危险。左侧下肢已经炭化。用手敲,硬梆梆的。血管也烧焦了,血管就像树枝形状,僵化凝固着。孩子休克了。”
“孩子上肢全是针眼,没法打针。包扎也很专业,显然在医院抢救过。”
病区进入紧张状态。
“切静脉。输蛋白血浆、输抗生素、输抗休克药物、输维生素。”
“全身检查。换药,重新包扎。”
孩子的父亲靠着床,蹲在地上,用手按着胸口。他的朋友去办住院手续。“我身上只有1000元,孩子她妈妈明天就来,带钱来。”办完住院手续,他的朋友说妻子也在住院,得走。孩子的父亲守着孩子。他站不住,他说三天没吃饭了,也没睡觉。他蹲着。
一个小时过去,孩子从处置室被推进重症监护病房。
孩子在输液。父亲在床边看着孩子。孩子又黑又瘦,脸上皴得厉害,或许是哭的原因,皴的地方甚至结了痂。
父亲摸着孩子的手、孩子的头,孩子昏睡着。他趴在孩子的床边,看她的脸。他两眼充血。
父亲在孩子的床边趴了40分钟,孩子始终睡着。
“我要吃点东西。”父亲一脸痛苦,只在登记表上写了孩子的名字:李霞,年龄:一岁半。家庭地址:四川内江。就捂着胸口,要下楼吃饭。
父亲走了。从五楼的楼梯走下去。
有护士下楼去,在三楼楼梯口看到他。他趴在栏杆上吐,吐完了,一直趴着。
他的表情痛苦而伤心。
他没有来。他再也没有出现。他把自己的孩子,一个人,留在医院。
“孩子处于休克期。四肢发冷,血压低,心率快,发烧,39℃。”乔骋主任说,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”
一天、 两天、三天,孩子的情况在慢慢好转,孩子的家人杳无音信。
“3月12日,上午8点。我们给孩子进行**次手术。”
手术必须尽快进行。孩子左下肢被火烧坏的部分深达两厘米:皮肤——皮下组织——浅筋膜——脂肪,只有深筋膜、肌肉、骨头未曾伤及。
“坏死组织是病灶,是细菌繁殖的土壤。休克期过了,要立即动手术去除坏死组织。”
3月12日的**次手术是对左下肢进行切痂——清除坏死组织,然后敷上生物敷料。3月15日进行植皮手术。从孩子的头上取下7%的皮,植在她的左下肢。
3月23日,对右下肢进行切痂。
3月28日,对右下肢进行植皮。
“手术都很成功。”乔骋主任微笑着说。
孩子的家人一直没有出现。
孩子不会说话,只会喊“爸爸、妈妈”。偶尔喊一声,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,或者哭泣。不笑。不知道是因为痛苦,还是因为对于陌生人的恐惧。
没有人知道孩子到底是怎样烧伤的。孩子父亲当时的描述是,妈妈不在,他们住在二楼,他上厕所。发现起火了,跑进来,孩子就烧成这样。他没有带病历,说全部忘在了出租车上。他除了登记的那点点不知真假的信息,没有留下任何资料。
“他的说法太简单,对于起火的原因,被烧的当时情况,我们一无所知。从孩子的伤情来看,火源在她的左下侧。令人难以想像的是,孩子被烧得如此之重,至少被烧了有四五分钟。这么长的时间,孩子为什么没跑,为什么没人救她?孩子一个人在上面,怎么会燃起这样的火?”
由于忙于抢救孩子,没有人想到仔细盘问。当时火灾情形只能猜测,无法证实。知道内情的孩子的家人竟然从此全无音信。孩子在遭受火烧之后,又失去了*亲的人。
“我喜欢女孩。”他的父亲曾这样对护士讲。
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而他所喜欢的女儿,一个一岁半的孩子,独自承受着身体的痛苦,无助地在痛苦中喊着“妈妈”。
医生、护士,完全打乱了自己的工作规律。她们要给孩子买牛奶、买“小馒头”、买尿片,甚至小玩具。她们要给孩子喂奶、把大便小便,她们要明白孩子的哭,是因为疼痛、饥饿还是恐惧。
“我们3个人,24小时轮流值班。”烧伤科人力紧张,可是孩子现在成了中心。
4月6日下午,我站在孩子的床头。孩子紧张地看着我,眼睛圆圆大大的,惊恐不安。给她东西,她的手一动不动。只是惊恐地看着,嘴一扁,哭出声来。护士给她喂小馒头,她噙着泪,停止哭泣,眼睛还是紧张地看着病床边的不速之客。
她已经是个漂亮的女孩了。“跟刚来的时候不能比。”护士说,“她会笑了,昨天笑了一次。”
总有病友来看她。吊着手臂的、驻着拐杖的。他们静悄悄地站在她的床头,看一会儿,再悄悄地离去。他们在过道中叹息。
乔医生又来看她。孩子哭起来。“她怕我。”乔医生说,“给她换药。每次总是十二万分的小心,用消毒水把纱布沾湿了再揭,肯定还是会疼。”
孩子大声地哭。隔壁病房的一个小伙子,拿了自己的随身听,放在孩子的床头。音乐缓缓飘动,孩子奇妙地安静下来,眼睛盯着。音乐响着,孩子的眼睛渐渐蒙胧。睡着了的孩子,不知道梦里能不能见到她的妈妈,她的爸爸。
“明天还要动手术。”乔医生说。
4月7日,8点。住院医生、护士,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孩子的床边。今天,是孩子的第五次手术。“手术成功,这就是*后一次手术了。”乔骋主任说。
孩子身上被烧坏的,没有植皮的地方这次全要补好。
住院医生剃去孩子头上的头发,用刀刮成光头。手术中要从这里取头皮,植到她的身上。“头部血供好,头皮再生快。另外,以后头发长出后,完全看不出伤痕。她是个女孩。”医生说。
女孩哭了,轻轻地。她也许知道会发生什么,也许不知道。她都会哭。
8点36分。护士把孩子推进电梯。手术室在7楼。3号手术室。
孩子被送进手术室。围着孩子的只有医生,还有我。家属等待区的走廊里空空荡荡。
一个夹子夹住孩子细小的手指,监视器接通。很普通的夹子显得很大,不知道孩子的手指会不会很疼。
心率正常,血氧饱和度正常,血压正常。
“给氧。”护士给孩子接上氧气管。
“麻醉。”麻醉主任给孩子实施全身麻醉。
两位担任助手的住院医生拆开孩子身上的绷带,开始对创面用碘伏清毒。一定很疼。
医生轻轻拨弄着金属器械,碰撞的声音让我的心一阵阵发紧。我盯着孩子的眼睛。亮光在她的眼睛里慢慢地消失,像渐渐地小了并终于熄灭的油灯的火苗。她的眼睛完全失去了光亮,眼角噙着泪,无声地望着天花板。
“孩子睡着了吗?”我问。
“不是睡着了,是麻醉了。”
孩子的眼睛慢慢地合上,手术要开始了。
手术室充满监视器发出的孩子的心跳声。怦、怦、怦、怦,声音不大,可是非常有力,非常稳定。每分钟145下。
9点50分。孩子身上的伤口清理完毕。血袋里的血一滴一滴地滴进孩子的体内。“为了防止失血过多。昨天夜里已经输了75毫升的血,现在还要输225毫升。”乔主任说,“孩子太小,身上血量少。”
10点10分,乔主任开始在孩子头上取皮。怦、怦、怦、怦,脉搏正常。孩子安静地熟睡着,什么也看不到,什么也不知道。我退出手术室。她只是一个一岁半的孩子,这个孩子现在正遭受的一切,我不敢面对。穿着无菌的白色大褂,我突兀地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。
孩子在7楼手术室。5楼,她的病房里空空荡荡。病床上洁白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,一尘不染。一个布娃娃放在枕头旁边。那只随身听悄悄地,摆放在床头柜上。
12点30分。从孩子被推进手术室到现在,已近4个小时。
乔骋主任开门出来:“手术顺利。”
4月8日。
护士给孩子喂着稀饭。“她能吃不少。”护士小姐给我看她手中的杯子。孩子看着我,眼神鲜亮。
孩子的腿还是用绷带吊在支架上,两只手也用带子拴着,怕她乱抓。她的头可以动,眼睛可以四处张望。
“再过一个月,就可以出院了。”乔主任说。
乔主任所说的出院,是指通常意义上,有家的人。
没有人知道,一个月后,等待这个孩子的是什么。
她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便是孩子曾在句容人民医院治过。可是经过调查,句容医院没有收治过这样的幼儿。
她无处可去。
“孩子出院后,要护理,要帮她锻炼。路还很长。”
“以后,她能走。她的手没有问题,她的智力不会受影响。她能自食其力。”
“但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样。”
从乔主任办公室出来,我再去看孩子。
“她一直喊着妈妈,喊个不停。现在睡了。”护士说。
孩子睡了,脸贴着布娃娃的脸。护士用湿纱布擦去她脸上的泪痕。
“她还要经历很多痛苦。每年都要做一次手术,直到发肓成熟。”医生说。
她才一岁半。
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,因为采访对象已经走进我的内心,影响着我,牵扯着我。我是一个幸福的4岁女孩的父亲,我为另一个陌生的不幸宝宝而痛苦,她的痛苦我甚至感同身受。因为这,我想替她,感谢这些善良的人们,并且记下他们的名字——虽然,也许他们并不需要:南京红十字医院烧伤科的乔骋主任,是他给孩子带来新生、医院工会郭明主席,是他的奔波呼喊,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孩子;还有烧伤科医生:杨永胜、陈勇;护士:王燕,丁小燕、田亮、梁凌虹、仝开棉、兰志红,她们是真正的天使,是她们把孩子从噩梦中牵引到温馨的人间。感谢的名单中还应列上没有留下全名的钟小姐,她为孩子带来了**笔捐款。还有小李霞的病友们,他们给了孩子*贴近的温暖。这个感谢名单很不完整,因为只要用心去关注孩子的,哪怕为孩子的命运有过一声叹息的善良的人们,都体现着人性的美好。
*后,我想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一句:孩子她想你们。痛苦时,她呼喊着你们,恐惧、饥饿时她喊着你们,她在梦中喊你们,在无助孤单时,她要你们。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年半的时间里,她*亲的是你们,她*可以依靠的是你们。*疼她的,也是你们。
也许,你们有着自己的无奈,也许,你们有着太多不得已的理由。可是谁都没有权利让一个无辜的宝宝永远哭泣。请你们给孩子一个未来,不要让一岁半的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,永远找不到爸爸、妈妈。
她想回家。
(经过多方努力,两年之后,孩子终于被一个合适的家庭收养。她家的附近,就有一座大型医院。)
孤儿院
天亮了,打开门,一个孩子被用绳子拴在孤儿院外面的栅栏上。孩子裹着棉衣,也许是哭累了,躺在泥地上已经睡着。一脸的泪。
2006年9月19日。
在安徽颍上到阜阳的102省道110公里处,一面旗子,高高地插在树桠里。没有风,旗子贴着树干一动不动。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旗子的下面,努力朝远方张望着。
他说,我就是王家玉孤儿学校的老师。
“孤儿院在河的对岸。”他用手指指。
一群母鸡在学校门口的草垛下面刨食,对于来人毫不惊慌。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笑着喊着,奔过来,打开院子的栅栏门。接着有更多的孩子涌过来,朝我们拍手,笑着,喊“欢迎”“欢迎”。
推开校长室的门,木头门发出吱呀的怪叫。一位老人闻声从墙角的行军床上艰难地爬起身。
他说,是的,我是王家玉。上楼梯的时候,这位67岁的老人摔了一跤,腰部骨折,已经卧床两个多月。
老人从昏暗的角落里走到透着阳光的窗户跟前,笑着,笑容落寞而沉重。孩子们的小脑袋在窗口挨挨挤挤,不一会儿,上课的铃声响起。一哄而散。
这个简陋甚而寒伧的校园里,生活着214个孤儿。
孩子们在上课。
一年级的课桌是一块块的木板,铺在水泥墩上。孩子们看到了我,齐声地,把拼音读得格外的响亮。
秋日的傍晚,风里已经透着阵阵的寒意。高声读着拼音的六七岁的孩子们,绝大多数还穿着拖鞋和凉鞋。
一年级教室的后面,是聋哑孩子的教室。孩子们在画画。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,美得让人心痛。因为他们之中,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。孩子们更加的刻苦,他们有了希望。
而在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,三位老人手里抱着,车里推着五六个几个月大的孩子。都是残疾孩子。
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,来这里帮忙的。
“想到这些孩子,我就忍不住眼泪。我在家里什么也干不了,我天天来带他们。”
他们都是孤儿。214个孤儿。他们,每一个都有着言说不尽,甚至无法言说的可悲身世。然而,他们看上去,几乎是快乐的。他们的笑容热情而腼腆,他们的眼神单纯而清澈。也许,在经历了太多灾难的之后,衣食无忧,就是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全部含义。
孤儿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绿岛,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。
1994年。
“我到颍上县城去办事,五六岁的一个孩子,在垃圾堆里扒东西。办完事回来,他还在那里扒。我说,孩子,这里东西脏,不能吃。我买了两个烧饼给他。后来,几次来县城,都遇见他。就每次给他买两个烧饼。他一看我,就跑过来。亲热得不得了。我说,算了,你干脆跟我回家吧。”
“他父母都不在了。后来,他大了,送他学了汽修。现在在苏州工作了。”
“他是我收留的**个孩子。”
谁会在意,在广大的城市乡村,处处都有流浪孩子的栖身处呢?王家玉总是能发现他们,他们也总是对这个面容和善的老爷爷充满不同寻常的信任,这真是难以解释的现象。王家玉亲自发现收留的孤残儿童,在四五年间,竟然有二十来个。安徽阜阳颖上县的这个行为不合常理的农村老汉,一下在四里八乡出了名。出了名的结果,是更多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。到了2003年底,王家玉的孩子,达到了183个。
王家玉出生在贫困县*穷的农家,家徒四壁,少年丧父,三十岁才娶上了患有癫痫的妻子。因为妻子无法料理家务,王家玉远赴东北做伐木工人,竟要背上两个弱智的女儿。能吃苦的他,凭着木工的手艺,开办家具厂,1994年,他的家底有了四、五万,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。到了2003年,他的收入增长到几十万,而孩子增长速度,又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。孩子,让他的厂房,变成了校舍,让他的全家和工人,成了护理员和厨师,更让他本人彻彻底底,从富翁,变成了还有大批欠款的穷汉。
……
猜你喜欢
-

- 【系列自选】儿童科普百科书籍 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籍中国幼儿百科全书 漫画中国 套装共12册
- ¥ 102.8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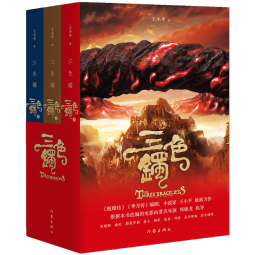
- 三色镯(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编剧王小平最新力作 关晓彤 姜文 胡军 苏菲.玛索主演电影 全3册)
- ¥ 64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
- 乐乐趣 低幼启蒙互动手偶书 适龄0-3岁 亲子互动小帮手 促进宝贝多元发展 【手偶书】小兔巴尼
- ¥ 39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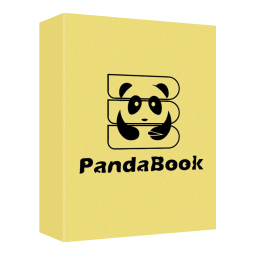
- 阶梯图书馆:小学生通识教育读库 全40册
- ¥ 278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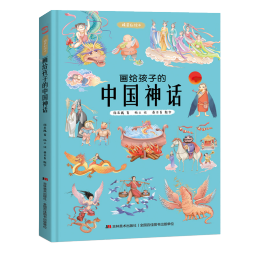
- 画给孩子的中国神话 : 精装彩绘本
- ¥ 41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
- 张信哲 字私(首刷附張信哲限量明信片組) 张信哲 字私(首刷附张信哲限量明信片组)
- ¥ 200.8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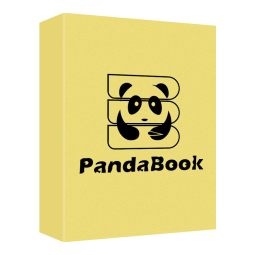
- 近代文学批评史(全八卷)
- ¥ 1078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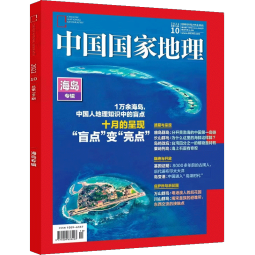
- 【加厚10月特刊】现货包邮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海岛专辑 2022年10月刊 旅游地理百科知识 人文风俗 杂志铺
- ¥ 22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
- 【全国获奖绘本】儿童暖心获奖绘本系列8册幼儿园儿童绘本3-6岁
- ¥ 28.7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
-

- 人间失格精装典藏版
- ¥ 16.3元
-
2年前 京东领券购买